个体叙事、时代描摹与精神探询 ——罗伟章小说的三个维度
在多年的创作中,罗伟章逐渐形成了自己较为恒定的文学风格,他的小说包罗万象、涵盖万千,从微观生活世界到宏观精神领域都有所涉及。个人、时代与精神构成其小说的三个层次和维度。从人的描摹,到时代书写,再到存在的探究,三者之间有一种层层推进的逻辑脉络。
一、个体叙事:农民书写、底层关注、现实思考与人性深描
罗伟章的小说十分关注现实,聚焦每位个体面临的生活现实问题,尤其是关注农民这一群体。作为个体的农民是罗伟章笔下常见的人物,通过个体的书写来呈现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罗伟章对农村衰败问题、对农民工问题、对教育问题的关注,都是对农民生存问题的关注。”1《大河之舞》书写农民罗疤子一家人的生活遭际。女儿罗秀被人们看作“疯子”,一直没嫁出去,却意外怀孕,生下女儿之后就去世了;因为姐姐的突然离世,弟弟罗杰也疯癫了,罗疤子也渐渐活成了一个“窝囊废”,与巴人好斗尚武的传统渐行渐远。虽然不断闪回到这个族群的历史的书写,小说整体上还是聚焦在普通个体生存史的描摹上面。小说最后写到,数年之后罗杰回到家乡,已具备了改变半岛面貌的能力,他游说镇里将半岛打造成古巴人遗址和农业观光旅游区,这也是回到现实回到生活的书写。《饥饿百年》以一个老农民的一生为缩影,书写了百年“饥饿史”。《饥饿百年》中的农民形象“父亲”很典型,身为农民的父亲卑微坎坷、坚韧不屈,为了这片能生长庄稼和让他生儿育女的土地,为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卑微而坚韧地生活着。
《谁在敲门》也是一部聚焦农民个体的作品,对农民众生相有深入的描摹。作品涉及众多的人物,既有整个许氏家族的几代人,也有通过许家人彼此交际引出的具有关联的其他人。小说的出场人物上百个,每个人物都鲜活而形象,立体而丰满。核心人物父亲是“中国式父亲”的缩影。许家父亲在中年丧偶之后,一个人将七个子女拉扯大,可无论他怎样努力,毕竟能力有限,总能被人挑出毛病,在那样生活较为艰辛的年代,甚至不得已将第七个孩子送人,而他自己也有很多传统农民固有的特性,比如任劳任怨、节俭的优点,又有絮叨、固执、胆怯的缺点,抑或是关心生存能力较差的“老幺”落得偏心的形象,都十分真实和典型。母亲形象虽然没有直接书写,但在零星的书写中也较为清晰地将其呈现了出来。小说还写到许家的第二代人和第三代人,这些人物依靠父亲这一家族的“大家长”串联起来。
罗伟章是一个深切关注现实、极为注重日常生活书写的作家。这其实和“底层书写”接续了起来。罗伟章早期创作与“底层写作”这一潮流密切相关,他也被归为底层文学那一流派,“以写作底层著称”2,之后他的很多作品大都聚焦日常,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人情伦理、社会现实、儿女情长构成小说的基础,形成个体叙事的肌理,从农民群体,书写到各种人群。在罗伟章笔下,始终聚焦个人及其家庭面临的教育、医疗、就业等现实问题,农民、进城务工者、个体户、小手工业者、小包工头等群体是他反复书写的人物。“罗伟章对于社会下层的日常生活非常熟悉,一支笔枝枝蔓蔓地蔓延着各种社会传说,人际关系,枝节上套枝节,总是把小说场景呈现得非常广阔。”3正是这份熟悉,让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及物性和接地性。《奸细》以地方中学“择优”“掐尖”书写教育问题;《我们的成长》探讨教育与成长的问题;《大嫂谣》书写农村女性大嫂苦难的生活;《河畔的女人》书写一群因为丈夫外出务工而独自在老家撑起家庭重担的女性,精神与身体的双重苦难折磨着她们;《不必惊讶》中,贫穷是农村的主色调,经济、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条件都十分落后,贫瘠的土地生就了斤斤计较的人;《寂静史》以现实世界中的旅游开发为切入,种种旅游景区的打造模式直指现实;《谁在敲门》涉及教育、医疗、拆迁、扫黑除恶、扶贫、城市化浪潮等很多现实问题。这些都是对底层生活的直接描摹。
罗伟章的很多作品是苦难生活的直接呈现,并且用不同的作品对此主题进行了反复书写。《河畔的女人》中,女性们即使在例假期间也要下田干力气活;《不必惊讶》中,生病的人未能进行医治而被“活埋”;《星星点灯》中农民进城处处碰壁,最终走向绝路;《声音史》中,贫困的代课教师为了保住津贴不得不忍受屈辱;《谁在敲门》中,人们在疾病面前不得不考虑成本而放弃治疗;《镜城》以一个剧作家的都市漂流的梦境来书写生活的艰辛;《从第一句开始》中的陈小康在生活中不断计算,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从第一句开始》对生活的艰辛进行了全方位的呈现,具有集成性和代表性。虽然主人公的身份较为特别,但是其遭遇的生活却和普通大众是一样的。小说以第二人称向倾听者讲述一个作家成名前的一段极为困顿的生活经历。这是日常生活之艰辛的普遍呈现,虽然人物身份的特殊导致呈现的极端化,但仍是一种深切的现实关注。陈小康的成长史,从中学时代的求学,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再到有了家庭孩子,直到成名成家的经历过程几乎是每一位个体相似的人生路径。工作、离职、应聘、租房、装修、子女入学……柴米油盐、衣食住行都是芸芸众生必须面对的日常。
罗伟章的作品在书写小人物命运的时候,往往以小见大,以《谁在敲门》为例来看,虽然这是一部大部头的作品,皇皇数十万字,但由于聚焦个体,其切口较小,整部作品仅围绕三个核心事件展开,一是为父亲庆祝生日,二是父亲生病住院,三是父亲的葬礼。都是日常生活的常态,正是这三个事件,铺陈出了60余万字的篇幅。在描写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除了书写许氏家族人的动态,牵扯出每一个人物背后的故事,还旁枝斜出引出其他很多的人,有名有姓的人物就上百位,书写的内容更是涉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幅乡土社会的“清明上河图”。比如在医院的事件中,以“父亲的病”为引子,将子女们的内心世界一一暴露出来,演绎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千年古训,特别是在落后的地区更为凸显,因为涉及很多共通的问题,与时代挂上了钩。由生病倒查原因,则是由生日宴会引起,生日宴会也透露出生活的百态,从选择在谁家过生日,到生日的排场、各个晚辈的登场表现,到最后的“追责”,都是极具生活流的叙事。
新近作品《隐秘史》仍书写乡土主题,依旧是对人性的深度拷问。《隐秘史》以一个扑朔迷离的凶杀案作为追溯人物内心世界的窗口,让主人公桂平昌进入故事叙述的圈套之中,同时开启了人性自我发现的通道,由此深入到人物“隐事实”的书写中,让人性在自我修复和自我确认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以一种更加恢宏的时空概念打开了人的内心世界“隐秘史”4,人性依旧是作品的关键词。这样的主题在《星星点灯》等作品中已有表达,在《星星点灯》中,人性的丧失有着个体和外界合力的推动。罗伟章是一个反思型作家,一直在探寻写作的“小径”,经常将笔触伸向那些隐秘而阴暗的角落,尤其是擅于剖析人的内心世界,将人性描摹得淋漓尽致。一位位个体的书写构成了一种群像,也由单个的人指向了人所生存生活的时代,从农民的生活描摹到乡土社会的转型裂变,直至上升到现代性等问题,具有一种浓郁的时代感和历史感。
二、时代描摹:乡土和城市化、现代性与历史、大河小说与时代意志
罗伟章强调个体,更强调时代,“我们处在大的变革时代,每次变革都牵涉到许多人的命运,都是作家创作的宝藏,但问题在于,如果作家丧失了文学立场,社会变革出现在作品中,没有对千差万别的特定对象的关照,没有对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的关照,没有对低处的生命和命运的关照,作家下去体验生活,没有把体验到的生活与自己的经验、感受、思考和个性熔为一炉,就无力构成文学表达的生活。世间的所有事物,如果不能引发疑问,就很难谈到生命力,作家的使命,正是对疑问的注目和探寻”。5也正是这种时代感使得作家时时刻刻保持着这种对时代的关注和思考,也就会在作品中直接将时代作为基本主题,形成一种“大河小说”的品格。6
“人是一个个地活着,但人活的不是个体,而是时代。”7时代是罗伟章反复讨论的问题。《不必惊讶》书写普通的乡村生活,以一起看似微不足道的农村常见的“提前准备棺材”的事件,引发作者对现实和时代诸多的思考。《寂静史》的故事也和时代有关,除了 “挣工分”“土地下户”等具有历史节点意味的事件书写,还有当下“制造文化”打造旅游景点的时代特色书写。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时代主题也是以现实关注为首,《凉山叙事》《路上》等作品都是以宏大的主题切入现实和时代的。在《谁在敲门》中,时代的特性更为明显,“《谁在敲门》以生活的逻辑、复杂的网络、人性的幽微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丰富性与复杂性”。8“时代”这一关键词从题记开始就已经凸显出来,并多次回到这一点上。对历史与时代的不断回应,让小说具有“大河小说”的品格,时代因个体的累积而存在,个体也在时代的震荡中而存在,现实关怀上面,父亲在医院住院的描写中也指向时代,以父亲为中心,涉及多个家庭、多位病人的书写,从一个家庭的疾病问题,到整个社会医疗问题的思考,虽然兄弟姊妹们都有着较为优越甚至是富足的生活,但是面对重大疾病这样的堪称“烧钱”机器的东西时,他们还是选择了放弃治疗,原因仍要归结为物质层面,还是经济实力的不允许。乡土社会的各种特殊伦理、奇特而畸形的风俗,譬如对最后一个孩子(幺儿)的过分宠爱、兄弟之间的不合、女性所遭遇的家庭暴力、老人赡养问题等等,都指向时代本身。
乡土社会的书写是罗伟章对时代书写的主要着力点。《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声音史》《谁在敲门》等作品都书写到传统的农民与土地依附关系的解体,外出务工逃离土地成为必然趋势。有论者提出,“罗伟章的小说如实地反映了后乡土时代社会的多种样态9。“后乡土”的提法,正是一种城市化视域下的乡土关照。罗伟章书写乡村主题的作品始终有一个城市化进程的视角,作家关于时代的书写,集中在乡土社会的解体和城市化进程这一方面,农民与土地的依附性发生了裂变,这一主题在罗伟章的很多作品中都已经表达过了。
《空白之页》书写一个历史时段的乡土社会,作品通过主人公出狱后回到家乡所看到的种种破败之象来书写乡土社会的裂变。故乡的衰败、冰凉与戾气,使孙康平刚刚走出有形的监狱,又立即踏入无形的监狱。《声音史》通过乡村中某些“声音”的消失来书写乡土社会的消逝。对这种消逝,作者并不仅仅是抱着社会进步的形态,而是伴随着某种怀念。在作品中,杨浪用他的耳朵和嘴唇,把村庄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来。他相信终有一天,那些远离村庄渐次老去的人们,能循着他的声音,找到回家的路。这种颇具诗意的写法,其实是一种挽留和惋惜的表达。罗伟章的作品中几乎都写到了这种土地依附关系的解体,随着外来的影响,先进的机器在乡村轰鸣,人们习惯出门打工,再也不愿意回来,到了《声音史》中,村庄最后就只剩下孤零零的一男一女,“空心村”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谁在敲门》书写的也是近几十年来中国乡土社会的裂变。透过时代的描摹,营造出对乡土期望逃离又无法彻底割裂的一种复杂心绪。年轻一代的人们都渴望进入都市,摆脱乡土的束缚,但是总有亲人在故乡,自己的根始终在那里。由书写农民到乡土社会变迁的升华就是从个体到时代的递进。罗伟章“针对乡民之于现代性的抵抗和现代性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做出了生动感人的文学叙述”10。
作品的历史感也是时代关注的体现,历史的影子在罗伟章的小说中也始终若隐若现,作家对时代有一种历史化的描摹,用史学家之笔法在创作小说。《大河之舞》从历史写到当下,书写乡土社会的生存发展史,历史不会在这里拐弯,械斗场景中砍掉的耳朵和砍掉的脚就是这种记忆和见证。罗疤子等人物是时代的牺牲品,在喧嚣的运动后突然归于沉寂,前后经历对照的书写,既是民间伦理中的报应、轮回的宿命论书写,也是一种时代的潮流。小说开篇先有两段关于“巴人”的传奇性与真实性并存的引言,然后才开始了小说正文的书写,在小说中,也有“破四旧”“批斗”等历史活动的提及。罗疤子不再以武力的形式和罗建放决斗,而是承认了自己就是“脓包”,这种行为,其实是对巴人尚武的解构书写,也是历史不可阻挡的潮流,和他在特殊年代的英雄形象形成了对比。既有时代的关注,也有历史的意味。《太阳底下》是一部以历史为主题的小说,小说对“重庆大轰炸”进行了书写,但作品的重点在于二战史专家黄晓洋对曾祖母的死因之谜的探究,由此引发黄晓洋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导致妻子杜芸秋受不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只好另寻解脱和安慰。而黄晓洋走向崩溃,终于自杀。最终,安志薇的一封遗书和李教授在日本出版的一部著作,揭示了安志薇惊人的身份之谜,也揭示了战争刻写在人们心灵上的秘密。当然历史只是影子,人才是主角。正是这种以历史写现实的笔法,更能彰显个人与时代之关联,也能凸显作品的深刻性。
罗伟章延续了巴蜀文学的传统,注重文学地方书写,对巴蜀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多有阐述。罗伟章关于乡土的书写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是对地方文化的深度开掘,对四川乡土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方言、风物、景观、建筑、民俗、传统、文明在他的作品中都有体现。《大河之舞》对巴人历史的追溯,作品中的半岛是地方的代名词,半岛是一个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外面的人进入半岛心存忌惮。半岛人也戴着有色眼镜观看外界,巴人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群体,关于巴人的书写让作品有了种神性色彩。《大河之舞》关于巴人的讨论在作品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巴人的习俗、传承、流变、同化都被反复探讨。《谁在敲门》也是一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大河小说”。整部作品巴蜀风味浓郁,地方风貌、方言的使用、特色饮食(比如小说中大姐准备的那一大堆食物),都具有典型的地域特性。除了个人和时代的书写,罗伟章的小说也涉及一些关于文明、文化、善恶、生死等问题的思索,显然具有“清谈”的意味,而罗伟章对这些问题的思索直接指向精神世界的探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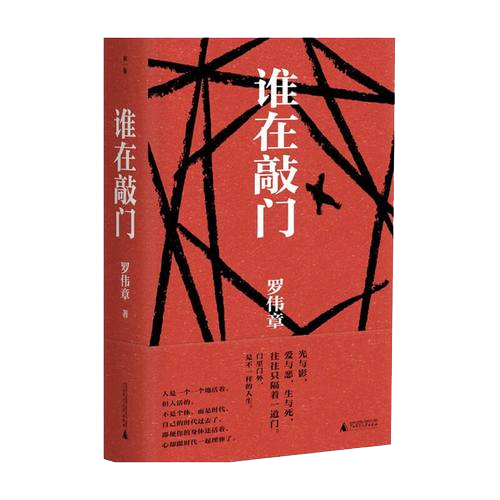
《谁在敲门》
三、精神探询:元叙述、清谈玄学、神秘主义与文学的终极意义
罗伟章的小说在个体与时代的关注之后,便来到了精神世界,探寻生命与存在这些宏大而抽象的命题,他的不少小说具有浓郁的思辨性,充满着哲学性。罗伟章的精神探询往往是在现实生活的书写基础上进一步思考,这种思考具有一定的通俗性,并非一种抽象的探讨,在日常生活事件的描摹之中,对很多形而上的问题进行了具象的思考,深奥博大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并未割裂。
“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11,这是小说的终极意义。“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指向人的精神领域。罗伟章在作品中关注了个体和时代之外,还有更多关于人的精神的形而上层面的思考。小说中的很多内容其实与小说的故事主线并无多大关系,但是作家用了不少笔墨和心思来进行讨论,将作品的高度提升了一个档次。比如很多时候,作者都要站出来讨论文学本身,无论是身份的设置还是故事情节,都有这方面的思索。《寂静史》借助当下各种旅游景区对文化的制造书写,借题对文化、传统进行了诸多思考。《从第一句开始》中叙述者和妻子不断有关于文学的争吵,这在现如今,是一种殉道般的举动,一丝文学还存活着的气息。争吵,也是“清谈”。清谈在《谁在敲门》中也多有体现,在父亲去世后,作家在描述葬礼的时候,进行了很多关于生死问题的谈论,这种模式就是典型的“清谈”。
因作家身份暴露而形成的“元叙述”手段是其精神世界探寻的首要的策略。在叙述方面,罗伟章的小说在视角上习惯使用混搭,将多种视角放在一起使用,《大河之舞》的大部分篇幅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但在书写罗杰学校生活的时候,“我”便以同学身份与之相遇。视角上的混搭带来叙述的丰富性,同时,作家喜欢使用“元小说”的策略,将作家身份引入作品中。罗伟章习惯使用文学家的身份,《从第一句开始》以回忆的方式书写了一位作家窘迫而真实的半生经历。作品的绝大部分内容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复刻,未经也无须太多的加工。小说主要内容是一个成年人面对困顿生活所必需的计算和算计,以及最终的失算。而失算的结果就是沉沦和妥协:自我沉沦,并向社会和命运屈服妥协。作家在书写个体命运沉浮的同时,也在书写整个时代的变迁。但这一切似乎很快就被解构了,因为叙述者跳出来说自己的记忆被毁掉了。因此,种种事件的真实性变得存疑了。小说整体上来说是一部围绕文学和作家展开的作品,叙述者的这种跳出来对作品本身大发议论的元叙述手法既是形式,也是内容。身份以及写作本身是一种颇具象征的行为,文学和作家的命运暗示并隐喻着回不去的过去以及未来那不可预测的生活和命运。
很多时候,作者都要站出来讨论事件本身,无论是身份的设置还是故事情节,都有这方面的思索。《谁在敲门》仍是一部作家型小说,不断出现作家的观点表露,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古老手法,有一种“微言大义”的味道,在不动声色中将很多问题直陈出来。譬如作品通过人物群像的书写,来描摹一种芸芸众生相,呈现世间百态。对这些人物几乎没有描写到超出基本生存范畴的东西。而关于这些缺失的东西,作家其实用了很多心思在进行阐发,由此也显现出一种悖论。罗伟章在小说中深入讨论了生与死的辩证,在小说中,不断有关于死亡的叙述,尤其是在父亲去世后的书写中,大量的笔墨与此有关,以此探寻一种终极的命题:生与死。“生”和“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大的事,正是对一个个生命的书写,来拷问生与死的辩证。另一方面,作品注重个体心理世界的开掘与深挖,注重人的精神世界的描摹,对精神世界的关注使得小说堪称一部精神心灵史。很多内容其实与小说的故事主线并无太大关系,但是作家仍用了不少笔墨和心思来进行讨论。比如对故乡的怀想与个体的寻根之旅,就上升到一种现代性的进程反思上。小说还有大量关于生命与存在的哲性思考。作家关注现实,更关注现实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走向人的精神世界,探寻灵魂深处的自我与他者。
在现实关注层面,作家只是一个普通人,到了文学这一元主题上,作家则显现出其独特的一面。不少小说都有作家这一身份的出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作家和文学的挽歌。在很多小说里,可以说将作家这一伟岸的形象彻底撕碎,露出真实而普通的一面。这种对作家和写作本身的反思,具有一定的讽刺性和很强的现实意义。《从第一句开始》中,作家开始将文学奉为自己心中的神,能够遵循自己的内心,到后来,不再翻书,也无心动笔,与约稿者的关系断绝,也是与曾经的自己告别。备受煎熬之后选择离职,却并未重新燃起曾经的文学之火。作家的经历经过回忆的滤镜,有些显得十分美好,比如狭小空间的阅读体验“心旷神怡”,可这些依然无法留住自己的初衷,反而对高档的酒楼、昂贵的礼品和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乐此不疲。记忆与其说是被动毁掉,不如说是自己主动放弃的,当他决定离开轩城南下的那一刻,一切的结局已经注定。这种时刻纠结着的前行,必定无法让自己的灵魂得到安宁,而不得不遗忘。作品围绕一个并不轻易下笔的作家展开叙述,是关于作家,关于文学的“元书写”。叙述者的妻子贾敏这一形象可以和他进行对比,中文系出身的她,似乎明白一切创作规律,却从不下笔,只是一味鼓励丈夫去写,不断提醒,“你已经多久没有动笔了”……叙述者因为记忆被毁掉,对一切充满着怀疑,不确定一个句子是否涉嫌抄袭,不得不一本一本去翻阅那上千册的书籍,而读者去对照文中出现的那些作品名称,似乎都有迹可循,也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些著作既小众,也经典,这种互文书写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写作本身的思考。从写作的本身而言,写作的困境一方面来自外界的干扰,生活琐屑之事的影响,也来自写作本身的焦虑。叙述者是值得深究的。对写作这件事请本身的反思。借作品的开头与结尾的探讨,来论述创作本身。写作肩负着为时间赋形的使命,甚至是置换生命、延续生命。陈小康和妻子贾敏数次的争论,都在探讨文学的本质,文学经验的本质。痴迷于一个句子的寻找,就如同朝圣一样,有了另外的含义。
《谁在敲门》的叙述者也是一位文学工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将其所有的创作进行了以此回溯与检阅,并预示了一种开启新的写作方向的可能。作家身份的使用,凸显一种个体的无力之感,也进一步暗示了文学的“无用性”。作为家族中唯一的“公家人”,给人以无所不能的假象,但他其实是无力的。叙述者许春明无法帮助大姐解决孩子的转正问题,面对父亲的疾病也无力阻止一家人的“放弃治疗”,对家族的很多年轻人,他其实充满着忧虑,但是没有能力解决,无力与无奈由此凸显出来。个人的无力指向的也是作家群体和写作的无力。《镜城》又是一部有关作家的小说,小说通过一场剧作家的梦境来隐喻作家职业本身的一种虚幻性,通过梦境来再次强调这一主题。
《从第一句开始》涉及大量的与主线关联不太大的内容,有典型的“清谈”意味。作品中有大量的辩证书写,父亲和儿子谁应该谅解谁的思辨、生命与死亡、苦难与幸福、高贵与卑贱、时间与静止、谎言与真实、纪实与虚构、作家与文人、作品的开头与结尾、时间里的故事与故事里的时间……乃至于这个人本身不同的生命阶段所具有的人格特质等,都有一定的对比度。在作家的笔下,万物似乎都成对出现,彼此、因果、相生相伴,种种对举,都没有绝对的逻辑依据,也就有了转化的可能。接下来,作家其实更进一步,将一般的哲思上升到更加神秘的阶段,不少句子如同谶语箴言,很多时候一语成谶。妻子贾敏的文学思维,一直没有出场的写作老师,都加剧了这份神秘感。思考时间、存在这一类形而上的问题,试图在作品中,寻找自己的同道。具有哲理性的句子不断闪现,“生活不是此时此地,而是经历沉淀,是自己过去的一部分”。“很多书只能提供皮肤上的美感”。“蚯蚓是不是昆虫?”一句童言无忌,反复被作家提及,这种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认知差异仍然回到哲理的思辨性,无所谓对错,只是一种认识的偏差。这种神秘性的描写,其实正是文学最为精彩的一面。
小说的神秘性也是精神世界思考的体现。罗伟章小说中的非自然叙事较为常见,文本体现出“神性”的一面。《大河之舞》就是一部“人性”与“神性”交织的作品。12作品中的罗杰在姐姐去世后被姐姐“附体”,对丧歌的迷恋,以及小说关于巴人的不少书写,都有神性的一面。这样的书写几乎在其所有作品中都能寻觅到,《声音史》将“声音”这一最接近神灵的物种进行了深度书写,以对声音极为敏感的人物杨浪展开,通过天籁、地籁、人籁的书写,来进行一种神秘性的书写,《寂静史》以现代社会的旅游开发为契机,叙述者接受任务去探寻古老的传统,对古老的祭司进行了深度采访,以此探寻隐秘的精神世界,小说中直接陈述,祭司也是医生,既医治身体,也医治灵魂,这是对精神世界的直接关注。作品写到具有法力的端公、祭司,用“法事”治好果果疾病的书写、同时,作品还借助对祭司的采访,进入现代人的内心世界,探寻到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收录在《寂静史》这本小说集中的篇目,基本都采取了这样的模式,以现实生活切入,进入隐秘的内心世界,思索精神和灵魂层面的诸多问题。《谁在敲门》中有梦里吃药治好了顽疾、犯忌讳遭到报应以及大量的民间传说、稗官野史,凡此种种,都体现出了罗伟章小说神秘性的一面。
罗伟章的很多作品都有这种神秘性的书写。比如《凉山叙事》中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现象,即大凉山民间的精神统治者毕摩。毕摩和苏尼,是彝族独特的神秘群体。苏尼相当于巫婆和端公,毕摩是彝人的心灵护佑者,彝族文化传承,毕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纵观彝族历史,毕摩接受的教育最严格最系统,这一群体独占经书,掌握哲学、伦理、天文、医药、礼俗、工艺等全部知识,在彝人婚丧、生育、疾病、节庆、出猎、播种等日常生活中,负责沟通天地与鬼神,因而成为彝族民众的精神统治者。13家支制度和毕摩群体,是彝族独特的文化现象,对彝族社会和彝民生活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神秘文化的引入,让作品有了别样的风采。就连早期《星星点灯》这样的现实题材的作品也有女儿遭遇绑架时和父亲心灵相通的情节。凡此种种,都体现出了小说神性书写的一面,体现了作家宏大而注重细节的一面。
罗伟章的作品对自然景观也有细致的描摹,这些风物在小说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其实也符合一种清谈玄学的文风。自然风景比人类具有永恒性,具有见证和凝视的作用,罗伟章小说中常见的“山”与“河”就是一种重要的设置。山川河流这些地理风貌的书写,以永恒的东西来书写一种物是人非的状态,给人以沧海桑田之感。罗伟章历来注重小说中的风景,他自陈《饥饿百年》是山的文明,《谁在敲门》是河的文明,这其实是对风景在文本中重要性的一种提醒。作家对此有进一步的区分,山与河是不可分割的,前者描写的是传统文明,后者是现代文明,两者之间是骨肉联系。14罗伟章的《谁在敲门》的后记中,也记录了景物带给他小说书写的灵感:“天空苍黄,如同逝去的时光,人,就这样穿越时光的帷幕,一步步走到今天。人是多么坚韧而孤独,又是多么孤独而坚韧。回想离开芦山那天,阳光明丽,路旁的芦山河,静静流淌,河岸的芦苇和灌木,在风中轻颤,倒影仿佛也有了力量,把河水拨出微细的波纹。四野安静,安静得连车轮滚动的声音也显得突兀。当时,我心里或许就响起过那种寂寥的欢歌。”15《大河之舞》直接以“河”命名,小说中有关于山与河的详尽书写,小说多次写到风景,并对其有精致的刻画,被反复渲染,景物作为见证者一直没有随着局势的动荡而改变。这种景物的刻画彰显了一种历史的恒定和人生变换的悲凉之感。其他文本中,《寂静史》有对大峡谷风物的生动刻画、《凉山叙事》有对大凉山风光的精确描摹、《声音史》有对千河口的细致介绍。风物书写看似闲笔,却在闲庭信步中将这种“清谈玄学”的飘逸文风传达出来。
“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就是一座精神家园”16,罗伟章的作品正是在努力搭建一座座精神家园。罗伟章的小说创作从1990年代末起步,那是一个精神较为匮乏甚至被部分人忽视的时代,市场经济、金钱至上、消费社会、物欲横流、多元主义等等成为时代的常见词汇和风尚。在文学领域,新写实主义、底层写作、青春文学、商业包装的女性文学以及其他各类畅销书的运作,都或多或少反映了这种重物质轻精神的局面,人文精神的失落成为一个反复讨论言说的主题。罗伟章则从一开始就注意到“精神”这一层面,从“人”到“时代”再到“精神”的层层推进并最终落脚于“精神”,是他一以贯之的书写策略和文学坚守。
结 语
在不同的创作阶段,罗伟章笔下的侧重点有多不同,随着创作的成熟,作家思考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但其一贯坚守和关注的那些东西并没有减少和削弱,只是思考的面更广、点更深。时代的大潮与个体的生存交相辉映,“大河小说”的品格与个体叙述构成了其作品的“经”和“纬”。关于个人的书写,秉持作家一贯的现实关怀,延续底层写作的文脉;关于时代的描写,从乡土社会出发,关注城市化进程带给乡土的裂变与解体,揭露与反思现代化带来的各种现代性问题;在对人与时代的思考之后,罗伟章进入人的精神领域,通过作家这一“元身份”的设置,用超现实的笔法、元叙述手段等,讨论生命和存在这些“形而上”层面的问题。在这种辩证叙事中,将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都直观化和具象化了。罗伟章一直在探寻文学的终极意义,这是一个潮流汹涌的时代,每位个体都被时代裹挟着前进,无所谓情怀、梦想、价值……文学,或许是仅剩的清醒。在时代汹涌向前的潮流中,传统的消亡、文明的缺失、人性的滑落、理想的破灭、信仰的坍塌,都被作家们一一捕捉到了。文学,成了一个问号,追问着一切,等待着答案的降临。作为思想型作家,罗伟章的作品中经常具有作家身份的人物形象,这种安排,是希冀文学有更大的力量,而他也一直在为此而努力着。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艺术提出的重要美学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ZD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 陈琛:《罗伟章乡土小说创作论》,《小说评论》2020年第2期。
2 赵学勇、梁波:《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流变与省思》,《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
3 陈思和:《寻求岩层地下的精神力量——读罗伟章的几部小说有感》,《当代文坛》2010年第1期。
4 首届“凤凰文学奖”颁奖词,见http://www.sczjw.net.cn/news/detail/4558.html。
5 刘小波:《 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2020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暨‘四川青年作家研讨会’”会议综述》,《当代文坛》2021年第1期。
6 刘小波:《大河小说的“经”与个体叙事的“纬”》,《文艺报》2021年10月25日。
7 罗伟章:《谁在敲门·题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8 李云雷:《〈红楼梦〉传统、生活史诗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罗伟章〈谁在敲门〉简论》,《当代文坛》2022年第1期。
9 房广莹:《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及调试——罗伟章小说论》,《当代文坛》2022年第1期。
10 徐兆正:《铭刻历史的声音——评罗伟章〈声音史〉》,《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11 [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12 罗伟章:《大河之舞》封底,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13 张艳梅:《罗伟章〈凉山叙事〉:一部恢弘的彝族史诗》,《当代文坛》2021年第2期。
14 15 罗伟章:《每个时代下的人们,骨髓里都敲打着古歌》,《文学报》2021年4月19日。
16 贺绍俊:《当代长篇小说的精神性》,《人民日报》2010年4月23日。
- 罗伟章《谁在敲门》:个人命运与时代形貌[2022-03-01]
- 论罗伟章的小说创作——从《声音史》到《寂静史》[2022-02-10]
- 《谁在敲门》: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大河小说”[2022-0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