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颗真正的文学之心写作 ——从读徐怀中长篇小说《牵风记》想到的

徐怀中 (1929~),河北邯郸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协。全国政协第八、九届委员,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委员、第五届副主席及第六、七届名誉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中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等。长篇小说《牵风记》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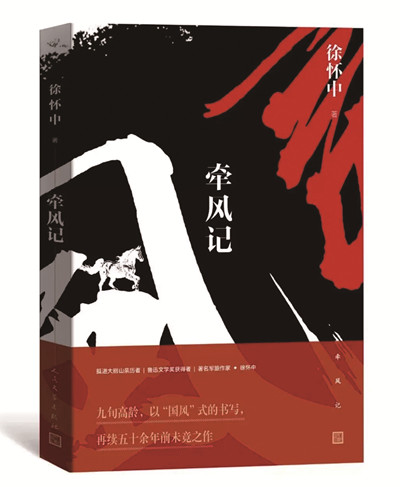
长篇小说《牵风记》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在小说出版之前,我就有幸读到了《牵风记》的电子版,这是作为我老领导的徐怀中部长,在作品未曾付梓之时希望听一听一众后学晚辈的意见。一种先睹为快的喜悦,阅读之后所产生的震撼以及对这位老作家的崇敬之情,皆可谓充盈于内心。当小说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中以高票获奖,深感此乃实至名归。老作家在其鲐背之年,竟能写出如此具有青春态、高质量的作品,内心里除了钦佩还是钦佩。这部小说的创作与出版无疑具有双重的意义与价值:一是其本身就是我国文学创作一个值得推重的新收获,能够获得国家文学最高奖“茅奖”这一殊荣即是明证;二是这部作品的创作实践与经验,对我国战争题材文学创作具有特殊的推动和启示意义。
徐怀中是我真正从内心里尊敬的老作家、老领导,他的人品、官品和文品有口皆碑。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加入革命队伍的他一生戎马又笔耕不辍,直至任职原总政文化部部长,衔授少将。他一路走来,或辗转许多岗位,或身居高位,都始终勤勉奋发,坦荡谦和,待人以诚,对部队的老中青作家皆多有热心帮扶、无私提携与诚恳指点,其亲和力与感召力令人印象深刻。同许多迭有新作、著述等身的作家相比,他的作品数量也许并不能算多,大致有《地上的长虹》《我们播种爱情》《无情的情人》《西线轶事》《阮氏丁香》《没有翅膀的天使》《那泪汪汪的一对杏核眼儿》《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底色》等。但这些作品皆为名篇刻石有痕,其中《西线轶事》名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首位,1983年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大奖;长篇报告文学《底色》则于2014年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其作品不仅显示出独具的创作风格与文学特色,在文坛独树一帜,而且在文学创作的观念与意识上,对我国的军事文学也具有启示性和领风气之先的意义。在其迟暮之年,虽然身体多病,仍以充沛的激情、时不我待的急迫,坚持着缓慢坚忍的“爬行”与掘进,“尽最大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击”,终于推出《牵风记》这样一部杰作。
也即是说徐怀中在其卸任之后,仍以极大热情恪尽推动军事文学发展之责,率先垂范。这部饮誉文坛的《牵风记》只有19万字,从其篇幅及获奖的事实来衡量,堪称一部超级精短的长篇小说。作品以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革命战争历史为背景,讲述了青年学生汪可逾、一号首长齐竞和骑兵通讯员曹水儿等主要人物和一匹名叫“滩枣儿”战马的故事。作者虽然不是对战争进行全景式的描述,但凭借其枪林弹雨、血火交并的亲身经历,“尽可能勾画出这次战略行动的悲壮历程”,并试图以自己丰富的战地生活积累,剥茧抽丝地制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使小说中几位主要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慢慢显影。作品的第一主人公汪可逾是个亮眼的人物,作为意欲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途经齐竞所在的“夜老虎团”驻地时,被阴差阳错地留了下来,一场混响着战争钢铁旋律的真纯美好、凄婉动人的人生戏剧就此拉开了大幕。怀抱一把古琴,弹奏一曲《高山流水》,无事爱对人笑,见谁都是一句“你好”,构成了这个人物冰清玉洁、人见人爱的外在形象基调。但她又是一个单纯倔强、做事认真的女孩,在战争环境中依然坚持在睡觉时将脱下的鞋子摆放整齐,固执地要给贴错对联的房东纠正错误,写宣传标语时努力增加其知识性和生动性并在字体上花费心思,对不堪入耳的无聊流言坦然笑对等等。她身为政治部文化教员或司令部参谋,又是众人瞩目与心仪的女神般的存在,是残酷战争环境中的“一道明丽灿烂的战地风景”。她虽被认为毫无心计,且有夜盲症和平足脚这两个对于军人而言明显的生理缺陷,其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与人们所习见的军队及战争生活有些格格不入,但在紧要关头她却能果断率领120多位身处窘境的女性北渡黄河,显然又具有胆有识、超凡脱俗、高贵完美的理想人格。作品赋予其“纸团儿”的乳名,是否包含着某种洁白而褶皱,脆弱而刚强的寓意与宿命呢?
齐竞似乎是置于汪可逾对面的一面镜子,是最懂得欣赏其天然美质的一个人物,同时也是因其而毁灭的一个人物。他与她之间并非是常见的英雄和美人的落套模式,这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留洋归国者既是军队团旅级有勇有谋的指挥员,又有着古典文化的深厚修养,他与汪可逾在战地环境中谈论古琴及乐谱诗词等话题,他所作的敌我态势观察报告她可以完整背诵其中多个自然段,他将自己的战马“滩枣儿”借给她骑等等,一次裸照事件使他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两人既是异性相吸更是同气相求,从而逐渐成为精神与心灵上的真正相通者,达到了神仙眷侣般相互钦慕的境地。汪可逾成为十分契合齐竞心中选择人生另一半的最理想的标准。可能读者对两人的情感走向会有一种极为自然而合理的期许,即按照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往下推想和演绎这首战地浪漫曲。但这个看似勇敢果决、英武完美的男人,正因为其内心过于追求完美,使其最终走向感情上的背叛之路,即当汪可逾同众姐妹们遭敌伏击被俘而被解救归来时,齐竞并不是首先关切和怜悯汪可逾的被迫跳崖受伤,而是质疑其于劫难之中贞洁的可能失去。齐竞的这种心理对汪可逾来说是无法面对和饶恕的。她清澈地洞明了他的这种卑劣心理:对于这个曾经深爱的而如今伤重在身的女人,要么是完好“干净”的,要么应该是一具尸体。因此她隐忍着巨大的悲痛表达了其极端鄙夷的情绪:“齐竞!我从内心看不起你!”这是小说最为沉重而沉痛的一笔。这样一个在战场上可以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亦不能突破某种观念的陈腐藩篱,置心心相印的爱情和生死与共的战友之情于不顾,从原有的情感立场彻底退缩,其本属完美的形象在伤痕累累的汪可逾面前轰然坍塌,进而一生都在追悔中过活,直到生命尽头。
骑兵通信员曹水儿这个人物似乎与齐竞的性格与生命轨迹截然相反,也与我们常见的战士形象大相径庭。这个因逃婚而出走从军、身材高大威猛的士兵,被齐竞看上后用一把勃朗宁从教导团团长手下换来做贴身侍卫。他在用心履职尽责的同时,私人生活上却颇为放浪不堪,其以白面换马料的伎俩沾花猎艳处处留情,行为上屡有出圈犯忌之处,以革命队伍的纪律来衡量无疑是个品质败坏的“问题”人物。就是这样一个士兵却慨然承担独自转运重伤在身的汪可逾的任务,从而反映出其勇敢机智、重情重义、铁骨铮铮的鲜明而闪光的特点。在长期男女独处洞穴危机重重的艰难日子里,这个原本登徒子式的风流人物,对汪可逾挖空心思、想方设法、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从未产生过任何跨越雷池的非分之想。这个人物因从内心“自惭形秽”,对汪可逾有一种“顶礼膜拜”的偶像化的效应,使其身体里存在的原欲因此荡然无存,才在那样的时刻和环境做出种种非常之举,其精神境界无疑是因情感的真挚和偶像的崇拜而神圣化了,其自身形象也变得越来越圣洁和高大。与其相关的就是那匹“滩枣儿”战马,它不仅能够读懂属于人类的情感,同人类进行心灵合一的交流,汪可逾弹奏的乐曲《关山月》居然也是其“最熟悉不过的”。汪可逾在曹水儿的指点帮助下,获得了对“滩枣儿”的“乘骑感”,并成为战争中生死相依的战友。这匹通人性的战马,还在队伍无奈射杀马群的惊险时刻,因曹水儿的放水而幸运地逃出生天;更为神奇的是,当汪可逾伤重不治离开人世后,这匹在大别山游荡已久的马儿,竟匪夷所思地找到了她,并将其尸身运到她生前最喜爱的银杏树的树洞里安放,自己却在奄奄一息、不曾气绝之时,就被成群的鹰鹫于瞬间啄成一副白骨。男人与女人、人类与战马,在烽火连天的大别山中,共同书写了一曲生命与人性的壮歌和悲歌。
汪可逾、齐竞、曹水儿这三个主要人物在小说中既是个性化的与过往战争小说中的人物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又具有某种符号化的色彩,代表了不同的人性和侧面,表达了作家欲寄寓和传达的认知与观念。作者在作品中所描写的这些人物命运和情感以及所涉及的种种场景,都是植根和依凭于其战争生活经验所进行的符合生活本身逻辑的书写;但又都是为达到小说艺术旨归的需要,进行了卓越、放胆的想象、虚构和夸张。如写120多位女性因过河载重的原因而褪去身上的所有衣装,写在危境之下为了不让战马群落入敌手而将其统统击毙,写汪可逾去世后遗体奇异地出现在树洞的魔幻场景,无疑都是作者虚构所为,使作品充满了出人意表的奇思妙想。但这些情节都有极强的动感和文学张力,超越了我们以往对中国战争文学的阅读经验,充分体现了在作者内心一贯葆有的纯净的审美趣味和对美好事物的真爱,以及在他的创作中始终坚持和体现的典型风格,即从人性、人情的角度切入战争生活,使其笔下的战争题材既残酷又传奇浪漫,反映出作者对真实美好生命的珍视与怜惜,让读者透过战争的狼烟、风云与血污中盛开出的真实生动、抒情唯美、质地异样的文学之花,认识和体验极端环境下的“英雄之美、精神之美、情感之美和人性之美”。同样应予注意的是,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其写作不是大河奔腾般的,更不是毫无节制的,而是字斟句酌、含英咀华般的,华彩而坚实、灵动而隽永,显示出作家非凡的才思与韵致,经得起仔细而反复的品读与欣赏。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呼唤具有更高质量的中国军事题材作品的出现。因为我们并不缺少战争的历史,不缺少战场生活的细节,也不缺少战争题材应有的内含。但我们似乎缺少一颗真正的文学之心,缺少对战争题材更为文学化、审美化的过程。审美能力的相对薄弱一直是中国的战争文学和以这一题材为主要方向作家的创作之短。《牵风记》所提供的有益启示或许是,作家不仅要把本身在写作上的优势通过作品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即作为战争的亲历者要有一颗细腻而非粗糙的内心,有一种个性化的而非共同性的视角,既看到战争中各种宏大和细小的影像,更看到战争中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把战争中的人、人的本性和人的存在意义,作为凝视战争生活的真正焦点,将通过观察和认识所获得的那一切,以文学的形式顽强执著地展现出来。而且不是仅仅从社会的或道德的角度去作机械的判断,而是根据文学创作的自身规律与审美需要,努力打破军事文学创作的诸多认知窠臼、思维惯性和同质化倾向,按照历史与人物的性格逻辑与固有样貌去写,甚至调整和放宽对特定情境中特定人物行为所持的评价尺度,进行具有极致意义的夸张与放大,进入写作上另一番可以纵横驰骋的自由空间,完成中国战争文学具有蜕变意义且影响深远的审美建构。《牵风记》所进行的就是一种战争题材文学新的审美建构,既体现了这位老作家的刻意追求,也是其写作实践的一次了不起的胜利。这次胜利是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而“回返零公里”的重新创作:“我的小纸船在‘曲水迷宫’里绕来绕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才找到了出口。”这是一段苦尽甘来式的创作心路历程的真实表达,也应是所有的中国战争题材作家应当持有的追求姿态。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在《文艺报》所开设的“文学观澜”专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2022年4月20日第5版。)

相关文章:
- 《牵风记》:“回返未来”的美学呼唤[2022-04-20]
- 梁晓声小说与当代文学中的两种知青形象[2022-03-18]
- 《人世间》的叙事雄心和史诗传统的再兴[2022-03-18]
- 河水与招魂:从《河岸》到《黄雀记》[2022-02-21]
- 《黄雀记》:作为性格悲剧的美学建构[2022-02-21]
- 培育中国当代文学新经典——茅盾文学奖40周年刍议[2022-01-26]
- “博物”美学与情感记忆的光泽[2022-01-24]
- 破局者:金宇澄和他的《繁花》[2022-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