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风记》:“回返未来”的美学呼唤

徐怀中 (1929~),河北邯郸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协。全国政协第八、九届委员,中国作协第四届主席团委员、第五届副主席及第六、七届名誉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中短篇小说集《没有翅膀的天使》等。长篇小说《牵风记》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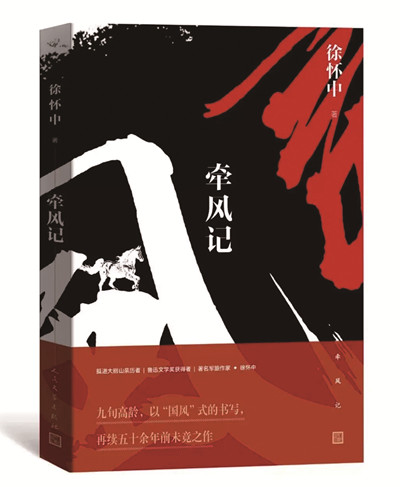
长篇小说《牵风记》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所有将笔尖对准战争的军事文学必然写到死亡,那些作品中的人物或死于一次壮烈的冲锋、一场毫无胜算的突围,或死于一次可耻的叛变、一颗荒唐的流弹。但我第一次在军事文学作品中读到《牵风记》中描写的这样一场几乎全由女主人公主动安排进行、象征意义远大于现实层面的精神性的非寻常死亡。
小说写到女主人公汪可逾临终时说,“若查阅《辞海》上的‘汪’字,品味那短短一两行注释文字,果真颇有些讲究的。‘深广貌。汪然平静,寂然澄清。’凡汪姓者,其内心空间自会深而广之,如一汪池水,平静息止不起涟漪;又当寂然不动,即入浊水澄清而明净透彻。”而当徐怀中先生让“汪”这一姓氏后配上“可逾”一名,又让“逾越”的“逾”字点化了人物在“如如不动”的性灵底色下总在“伺机而动”、无限向前的轰轰烈烈的行动性格。
汪可逾离开爱护自己的父母,身背包裹在锦缎琴囊中的宋代古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已令人吃惊不已。小说之初,“隆隆炮火中传来一曲《高山流水》”,是军事文学中罕见的战场情境。汪可逾的第一个“逾越”,就在于她敢于将自己的智识与性灵抛掷于战场,用她所擅长的琴艺去扶正颠倒,让能使心物交融的刚健、质朴的音律去提醒世人葆有对善与恶的省思,并坚持通过“我行我素”来调和因为杀戮和生命资源匮乏而造成的人性退化与精神封闭的状况。
正如她总会“高高举起臂膀,按到房门的上沿把门推开,随后背对房门,轻轻向后蹬一下,咣当一声,房门阖上了。”以避免用手接触门上最不卫生的人们频繁接触的部位;她会用一块白色小手帕托着每个月的团费去上缴,之后再洗净手帕;当发现地上两只鞋子摆得不整齐,即便她已经上床休息也一定会爬起来将鞋子摆正;哪怕借住于老乡家,看到房东大门上新贴的对联上下联给颠倒了,她也一定要纠正过来。
有了如上种种行为,汪可逾在过小河渡口时,坚决拦住要从十多具敌军士兵尸体上碾过去的马车而让剧团改道上游水面过河的举动才更让人感慨,原来汪可逾还要在你死我亡的修罗场上坚持“至善”,以进行她的第二个“逾越”。
汪可逾的执拗印证了她有着向人的最高精神演进的执著追求。极端的战争环境一次次在她身上焚去了她认为应当退卸的对物(琴)的执念,也点燃了她的内在智慧,让一名原本小小年纪就能登广告、收润格的知识分子女性,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学会了用洋铁皮扎毛刷子写标语,拿扫烟囱、挖锅底得来的锅烟子制作墨色颜料。当她因齐竞一番演讲而备受鼓舞,便自制炭笔,用“点画匀衡硬瘦,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的柳体书法写下标语,并以最通俗近人的方式向四邻八乡的父老乡亲做宣讲。在这里,作者写到汪可逾与围观标语墙的老乡们“彼此相通心心相印”的情景,让人感到,置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借着战场和行军路线的不断开辟与拓展,实现了真正的“开眼”看国家、看人民。
徐怀中先生借助自身的革命经历,曾在多部小说中写到西藏和云南等地的战斗与风土人情。如《卖酒女》一篇中写到云南边境上一个小小的街市皆东,还有《阿哥老田》中,借一名解放军战士的视角写到了居住在云南省边陲的哀牢山、无量山一带的苦聪人。当写到文中的苦聪孩子如何与“解放大军工作队”的“阿哥老田”相识时,徐先生写道:“那天,我在岩洞里捉到一只狐子,就把皮剥下来,搁在路口,藏到大树背后远远看着。有过路的人,想要这张皮子,多少放点吃的东西在路口就是啦。你可知道?我们苦聪祖祖辈辈就是这么做生意的,以物换物,以心换心。”短短几句话,就将苦聪人的风俗、性格置于读者面前。如果说“革命”的一面是“你生我亡”,那么另一面就是“你中有我”,从彼此打量、相互认识到寻得共识与平衡,以此相互借鉴和融合。正如汪可逾在战争中将音韵之美和革命的知识理论馈赠给群众,群众则将保存生命的智慧倾囊相授;她临死前,通过与陪伴身侧的半文盲的曹水儿进行极具思辨色彩的讨论,来为自己的生命标注句点,曹水儿则满心敬意地照护她直至终了。
不断有意识地逾越身份、阶层的认知与情感藩篱,让原本困囿于头脑和纸籍的学问放归于乡野和人心之间,接受“道”的试炼、养塑,让汪可逾的革命历程更接近她理想中的“齐物”。她牺牲时年仅19岁,却“经历几度烽火岁月,以及战争史上最残酷的所谓‘剔抉扫荡’”,以其在最为酷烈的战场上对至善至美的坚守,深刻影响了与她相识相知之人的命运走向,尤其是对她十分欣赏和倾慕的齐竞。
小说中如是介绍齐竞:“野战军共有四位留学日本的,一位担任总部宣传部部长,两位是纵队宣传部部长,第四位便是齐竞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盟创办了文艺杂志《东流》,推出具有进步思想的小说、散文,齐竞便是经常撰稿人之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齐竞回国到了太行区八路军前方总部,打定主意要历练成为军事主官。小说中也在“军事指挥艺术是铁血之气的结晶”这一章节中对齐竞的战斗指挥能力给予展现和肯定。但就是这样一位军中的“天之骄子”,却在战争胜利多年之后仍对过世许久的汪可逾念念不忘。写完祭奠汪可逾的银杏碑文后,以吞服40多片维C的方式离开人世。全书最后,在一片寂静无声的肃然中,最后一次“铜钟一般浑厚而又深沉的古琴空弦音”,与若干年前的战地往事遥远对应,汪可逾的第三个“逾越”发出超乎时空的回响。
钱穆先生在《人生十论》的《人生三路向》中说:“向外的人生,是一种涂饰的人生。而向内的人生,是一种洗刷的人生。”对于汪可逾来说,她短短不到20年的生命过程中,其思想一开始就是未经涂饰、全然解放的,从未背上过对人、人性的成见或偏见。当汪可逾跟随队伍在大雨中结束强行军,就自然而然地脱下衣服晾晒而光着身子睡在了一家门洞里的门板上。那时已是旅参谋长的齐竞起床后见到这一幕,竟被从前人体摄影实习的经历驱使,“只想着,‘一定要抢拍下来,一定要抢拍下来!’他从挎包里取出了他那架战利品破旧相机‘罗来可德’,顺手打开了镜头盖。”而就在齐竞摁快门留下“战地即景”的时候,汪可逾醒了过来。令齐竞想不到的是,汪可逾看着面前的齐竞坦然自若地说道:“首长,洗印出来,不要忘了送照片给我。”在这件事上,汪可逾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她清新、风雅的艺术化人格。
而在拍照事件之前,当齐竞安排汪可逾坐上自己的座驾“滩枣儿”,已有是非之人编排此事,汪可逾听说议论后,第一时间找到通信员曹水儿质问流言究竟何意?面对汪可逾的直截了当,就连一向嘴皮子功夫了得的曹水儿也甚是尴尬和难堪。可直到她琢磨出戏谑的含义之后,汪可逾只是一阵会心地大笑,“笑得前仰后倒无法控制”,跑回自己的住处时“还留下一串串笑声”。这让曹水儿百思不解的一幕恰可证明汪可逾“八风吹不动”的生命定力,利、衰、苦、乐也好,称、讥、毁、誉也罢,个人的尊严正如宇宙自然的庄严,何需自辩。
于是,当读到小说“黄河七月桃花汛”的章节,看到汪可逾指挥着并与准备乘船渡江的妇女们一起脱下衣服,只着内衣以便落水获救时,就能知晓这一轰轰烈烈的场景具有多么直指人心的效力。逻辑难以接近的,正是作者徐怀中先生亲身从战火中带出来的关于生死最切实的氛围和气息。
对比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汪可逾具有林黛玉的才、杜丽娘的情,而其驾驭生命的强悍行动力又显然继承了上古神话中女娲和精卫的精神原力。其以血肉之躯在对抗战争的酷虐时,赤裸的身体愈脆弱便愈能显示她将在血火洗礼中“衔木到中古”的毅力与勇气。正是这份勇气,让汪可逾被当地团练武装俘虏又被解救后,面对齐竞质疑她究竟是否遭受侮辱时直陈愤怒:“齐竞,我从内心看不起你!”从此后,一对璧人握手言别。不久,齐竞再见到汪可逾时,已是汪可逾“面容如初,自然安详”的遗体被军马滩枣儿驮运到银杏树的树洞之内——“终于他看清楚了,汪可逾头部微微偏向一侧,两臂松弛下垂,全身呈浅古铜色,骨骼突出的部位,在日照下闪放着光亮。”
《牵风记》中,好几位人物的死亡都令人印象深刻。比如曹水儿,因和地主的女儿有染而被诬告为强奸,要被执行枪决之际,曹水儿还与钟情于自己的女人嬉笑,在最后排枪一阵急射之时,踹开了扑上来殉情的女人,“语音含混不清地喝道:‘他妈的着什么急,看打着了老乡!’”死得血性偾张;不满13岁的小演员刘春壶被俘后,被推进坑里活埋,就在其“面部开始变形,五官也扭曲变形了”之际,还在翻着花样的痛骂和大笑,死得有模有样;小说中还有一位着墨不多的“反派”角色郭老参事,当听闻上级在战局决定性时刻对自己费尽辛苦得来的情报判断不屑一顾,便冷笑置之,将身体扑进一把平日“招待客人切甜瓜用的”美军匕首,全力奔赴本不在其职责之内的死亡。
而即便与死后肉身被鸟兽啄食一空的军马滩枣儿相比,也唯有银杏树洞中的汪可逾,似是将死亡作为了又一次长途路程的起始:“一条腿略作弯曲,取的是欲迈步向前行的那么一种姿态。她显然是意犹未尽,不甘心在两亿五千万年处停滞下来,想必稍事休整,将会沿着她预定的返程路线,向零公里进发,继续去寻找自己的未来。”她的死是脱离地心引力,向着生命常识的回归,具有挣扎着飞升的精神性与悲剧美。这样的死亡是超现实的传奇,是她向着肉身速朽这一基本事实的“逾越”,也是作者徐怀中先生笃定实现的一次美学突围,将对战争进行思考所能抵达的极限再向前推,并开辟了一个更高维度的视阈供人类审视战争。
2015年时,笔者曾与徐先生做过一篇题为“我的未来是回到文学创作的出发地”的访谈文章。其中徐先生谈道:“在我看来,人生也应当如是观,只能是回返未来。这不是说我们要爬回到树上,但是我们要有古人浑朴、无欲的精神。科学是向前发展的,不会回头看。毁灭人类的武器越来越厉害,无人机随时随地可以轰炸。到头来,人类前途只能是在自己觉悟的引领下回到原初,也便是回返未来。”
从此来看,尽管汪可逾死在人生发轫之初,但她同样展现了与生俱来的母性——她是战场上常识的孕育者和纯洁灵魂的葆有者,痛苦与磨难激发了她基因中在女性身上积累了数世纪的智慧。她看待自然、战争、人性时参照的时空坐标系中,有存在于地球上约两亿五千万年的银杏树,有相传创于史前伏羲氏和神农氏时期的古琴,有至少30万年才能形成的溶洞中100年才长高1厘米的石笋,也有似是从上古奔袭而至20世纪的“古代野马群”……如此无限广袤无限深远的眼界,使汪可逾一早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脱离了简单二元论非此即彼的狭窄视域。如是到最后,在汪可逾精神气息的“牵引”之下,与她相亲相近之人也终于穿越了“有限性”的封锁,于主动的死亡中寻获尊严。在无有重逢的归属地,与人之最初的心性团聚。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在《文艺报》所开设的“文学观澜”专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2022年4月20日第5版。)

相关文章:
汪守德 | 以一颗真正的文学之心写作——从读徐怀中长篇小说《牵风记》想到的
- 以一颗真正的文学之心写作[2022-04-20]
- 梁晓声小说与当代文学中的两种知青形象[2022-03-18]
- 《人世间》的叙事雄心和史诗传统的再兴[2022-03-18]
- 河水与招魂:从《河岸》到《黄雀记》[2022-02-21]
- 《黄雀记》:作为性格悲剧的美学建构[2022-02-21]
- 培育中国当代文学新经典——茅盾文学奖40周年刍议[2022-01-26]
- “博物”美学与情感记忆的光泽[2022-01-24]
- 破局者:金宇澄和他的《繁花》[2022-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