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思缱绻千年,《洛神赋》依旧鲜活

故宫博物院藏《洛神赋图》宋摹本(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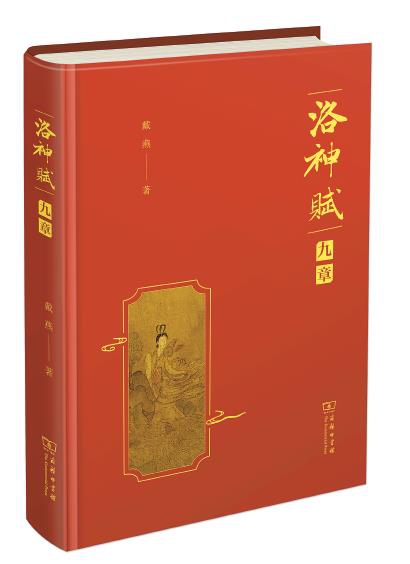
《〈洛神赋〉九章》,戴燕 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
《〈洛神赋〉九章》,是一部出语浅而根底深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见微知著的学术专著。它让专业的文史研究者读来豁然开朗,也让普通的大众读者读得兴致盎然。
是什么样的魅力,让《洛神赋》这篇三国时期曹植所作辞赋名篇,穿越时空,经久不衰?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复旦大学中文系戴燕教授,对它怀着长达十几年的研究兴趣,最后写出这样一本书?
对话戴燕,在感受《洛神赋》不衰的生命活力的同时,也体会到了藏于《〈洛神赋〉九章》背后,她对固有的文学研究范式的反思。
遇见《洛神赋》,是一个研究者的幸运
“如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让我始终怀着兴趣写完这本书
读书周刊:您专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史的研究,这段时期出了很多名篇佳作,您为何对《洛神赋》情有独钟?公开资料显示,您首次发表与《洛神赋》相关的文章至今,已有十余年。
戴燕(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作品入手,是做文学研究最常见也是最根本的方法,所以我平常多读作品,也在读作品的基础上,寻找合适的研究对象。我也习惯了针对具体作品或具体史料进行研究,就事论事,这样便落到《洛神赋》上。大概20年前,我写了关于《洛神赋》的第一篇文章,当然,那时的研究还很单薄。
《洛神赋》无疑是一个经典,不仅因为它的作者曹植在三国时代就是地位最高的作家,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被视为文学名篇,更在于到今天为止,它依然是一个“活着”的作品。尽管赋早已不是主流文体,现在更少有人写,可是《洛神赋》中的一些词句,比如“翩若惊鸿”“明眸善睐”“气若幽兰”等,今天还在被人们使用,而且在书法、绘画、戏曲、小说等领域,包括在影视这样的现代传媒中,《洛神赋》仍然是经常被利用的素材。它在这么长的历史中,有如此生命力、感染力,不断影响到后来的文学以及文学以外的创作,当然就很值得研究。而在研究它的时候,又必须要关注到材质不同的各种文本、媒介,因此需要有一种新的眼光,这些都很吸引我,“如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也让我始终怀着兴趣写完这本书。可以说,遇到《洛神赋》,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的幸运。
研究也是“复调”的,尽量提供开放式的思考
要打破文史哲的学科界限,将更广泛的史料纳入进来,让文学能够回到它的历史语境中去,以使对古代文学的解读,有更多实在的线索和支撑
读书周刊:这20多年里,您对《洛神赋》的认识过程是怎样的?
戴燕:读《洛神赋》,当然可以用大家都熟悉的文学赏析方法,讲它如何构成一部描写爱情的浪漫主义式作品,不过我是试着用了一个新的方法,希望能对此有一点改变。
实际上也是在做了许多年的学术史研究之后,我决定要有一点改变的,要尝试一种新的“观看”方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花了非常多时间去做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史叙述的调查和研究,其中也有反思,写成了《文学史的权力》。在那个过程里,我也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与方法,比如说我曾经讲在研究中国文学比较早期的历史时,应该要打破文史哲的学科界限,将更广泛的史料纳入进来,让文学能够回到它的历史语境中去,以使对古代文学的解读,有更多实在的线索和支撑。当然说说是容易的,怎么去做、做出来的结果好不好,还都要经过试验,我想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自己来做个试验。所以在反复阅读《洛神赋》时,也就特别注意与它相关的各种史料、资讯,后来觉得它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点,便开始写《〈洛神赋〉九章》。
读书周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文学史的权力》是从理论层面,阐述您的新的研究方法;《〈洛神赋〉九章》则是从实践层面,展示如何运用您的新方法。也就是说,《〈洛神赋〉九章》是您的方法论的一次演示。
戴燕:是这样的。我在大约十年前还写过一册小小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入门》,谈我对过去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认识,那时我说,在这个领域,过去的研究已经太丰富太精细,能够“捡漏”的地方不多。但是最近我开始意识到,也许因为我是“77级”大学生,我们读大学时,感觉有点“前无古人”“孤立无援”,就是没有什么师兄师姐可以依靠、模仿,但这也就养成了我们在精神上比较自由、在学术上不太受约束的习惯。几十年过去后,我发现在我心里也是有特别不愿意因循守旧的念头,这是时代留给我们的馈赠吧。所以,即使是在魏晋文学研究这么一个成熟的领域,我也不想“躺平”,总要发一点自己的声音。
读书周刊:《〈洛神赋〉九章》呈现了您哪些求新之处?
戴燕:我想归纳为三点。
第一,纳入更多的材料。我们读古代文学的人,没办法像读现当代文学的人那样,能够身临其境、带着自己的经验去理解,而是与文本隔着历史的长河,这很无奈。但是作为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搜集并利用尽可能多的相关史料,为古代文学重新建立起它们的历史环境,使得现代人在解读古代作品时,也能够遥想古人而有所依凭,做到真正的古今对话。《〈洛神赋〉九章》因此就涉及了文学、历史以及书法、绘画等不同类型的材料。
第二,引入新材料,是为了得出新的结论。如果古代文学研究在纳入新材料后,仍然只是重复过去的结论,这个研究的价值是要打折扣的。比如我讲《洛神赋图》和《洛神赋》的关系,如果只是讲了图是对赋的亦步亦趋的图解,那就还不够。我要分析图的出现给赋的读者带来什么样的理解上的变化,我想这才算是引入新材料而得出新观点。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新材料引入之后,还要在文学观念上有所改变。
读古代文学,我们都知道第一步是要识字,要通过训诂的办法来说文解字,由字到句,由句到段落、篇章,一步一步认识作品,看它有什么内容、中心思想是什么。可是这么做,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即认为这个作品是完整的、完美的,作者的创作是环环相扣、天衣无缝的。但事实是怎么样的呢?当然不是这样的,这其实是我们的想象,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几百上千年前的作品时,特别容易产生这种想象。
当我们引入更多的材料以后,比如对于《洛神赋》,我们就知道它是诞生在一个有关洛神的文学传统里面的。首先,当曹植说他受到了宓妃传说的启发时,那时的宓妃就不是只有一个形象,而有多个形象,刺激他写下《洛神赋》的,应该就是那些错综的甚至破绽百出的宓妃传说。其次,后人在解读、临摹、运用《洛神赋》的时候,作为传播、继承者,他们也不是在刻板地誊写、翻刻、改编,而这就造成了《洛神赋》本身,在它的文本内部,便有不少冲突和矛盾,在它流传的过程中,更是有正解也有误读。不过有趣的是,正是这种错杂纷乱的状况,让《洛神赋》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经典,时刻焕发活力。大概就像《庄子》里关于“混沌”的那个寓言,因为混沌,它是活着的。我在这里也用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说明《洛神赋》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一样,是多声部的复调文学。
因为是把《洛神赋》放在这样一个新的观念下解读,由此在每一章的写作里面,我也都用了开放的思考方式,并不寻求唯一正确的答案。
假使遵循唯一正确的“答案”,文学就丧失了趣味
它从很早的时候起,便为文学界与书画界所共享,共同结合成一个《洛神赋》的整体形象
读书周刊:《洛神赋》自诞生起至今已有千余年,仿若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您能简要描述《洛神赋》在漫长历史时期里被阐释、被误读的过程吗?
戴燕:先说文本。
现在能够看到最早的《洛神赋》,是在梁昭明太子编的《文选》中,然而对它的解读,自唐宋以来就有了分歧,唐代李善注《文选》引过一篇无名氏作的《记》,提出“感甄”说,认为《洛神赋》是曹植为了纪念甄后而写。唐代人是喜欢“传奇”的,他们大概很爱这种“索隐式”的阅读,将《洛神赋》与汉末三国时代的人物、政治牵扯在一起,揣度曹植隐藏在赋中的“秘辛”。
这是对文学的历史故事化的解读,在我们看来它或许牵强附会,可是它的影响特别大。随着“感甄”说日益流行,后来又有了试图化解它的“思君”说。
再来看画。
现在能够看到最早的《洛神赋图》,相传是东晋的顾恺之所绘。《洛神赋》转化为图以后,它的主角就从原来的宓妃即洛神一个人,变成了君王和洛神两个人,叙述者“余”的形象由隐而显并且格外突出,起码与洛神平分秋色。如果要给这位君王起一个名字,人们想到的自然是曹植。《洛神赋图》使得“她”和“余”的故事,变成了“她”和“他”的故事,强化了读者的一个认知,也是种误读——《洛神赋》写的就是曹植与洛神的邂逅。
最后聊戏曲。
1923年冬天,梅兰芳排演《洛神》,火遍大江南北,连病中的泰戈尔也一定要去戏院看一场,看过之后,还为之写了一首诗。《洛神》演的就是曹植与甄后的爱情,它让过去人们对《洛神赋》的误读更加深入人心,尽管学者们写了很多讨论《洛神赋》寓意的文章,为它究竟是表达“感甄”“思君”还是其他作澄清,却也丝毫不能动摇这个误读。20世纪关于《洛神赋》的这一段学术史,是与现代戏剧艺术的发展并行交错的。
读书周刊:对比2016年您发表的长篇论文《〈洛神赋〉:从文学到绘画、历史》,《〈洛神赋〉九章》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您引入了《洛神赋》书法史的研究。
戴燕:的确,涉及书法史的这一章是从未发表过的,这一次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处理。
为什么必须要写这一章呢?因为现在能看到最早的《洛神赋》是在宋代所刻《文选》里面,距离曹植写作已经过了几百年,也许有人会问:怎么证明现在我们看到的《洛神赋》就是曹植所写,而不是《文选》的编者伪造的?假如按照传统方法,只看文学文献,能够找到的线索有限,证据比较单薄,而用上书法史的材料,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因此,我在这一章就讲了《洛神赋》是怎样从三国时代起,便被书法家当成书写题材而反复临写的。我们知道书法史是很在意甄别书迹真伪的,我用的一些记载,也许入不了他们的法眼,比如大家都熟悉的王献之写的《洛神赋》,书法史家已经认定它是宋代人所写,可是放在文学史的研究里,这个真伪的争论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对《洛神赋》的每一次临摹、拓写、翻刻、影印,都足以代表它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我想要说明的是,正是由于《洛神赋》当年在东晋的王、谢两个大家族中,以文学和书法的双重形式被不断地效仿、复写,才使它的传播范围和生产数量一再扩大,更加成为经典。
事实上《洛神赋》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典,它从很早的时候起,便为文学界与书画界所共享,再加上图像,就像石守谦说的那样,“至迟至12世纪初时,《洛神赋》对人们而言,就不再只是一篇诗赋,而且同时是书法、绘画传统中的典范,它们共同结合成一个《洛神赋》的整体形象”。
读书周刊:从《洛神赋》到《洛神赋图》,再到《洛神》,既使《洛神赋》流传得更广,也局限了它,让人们对《洛神赋》的理解一再落入“感甄”的窠臼。您认为这些是对传统文本的丰富还是伤害?您如何看待现代艺术对古典文学的反向影响?
戴燕:尽管历史从来记载的都是胜利者的历史,但是看历史的人,却往往对失败者抱有巨大的同情。随着汉末魏初的那一段历史日渐遥远,曹丕、曹植、甄后等历史人物的形象在后人眼里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的人物关系也都有改变。曹植和甄后,在与魏文帝曹丕的关系中都是失败者,这两个命运相似的人物,就这样被牵连在一起。“好事者”想象他们曾经相濡以沫,制造出两人的爱情、悲情。
这种解读,就像人们说的是“歪楼”了,但无论正解、歪解、错解,都是在强化《洛神赋》的经典地位,只不过构成了彼此错落、高低不同的声调。好的文学,永远是“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吧。
作为研究者,我完全接受这种“歪楼”,因为这不但能说明《洛神赋》总是有魅力的,也实际上构成了“洛神”文学丰富的传统。我们要做的,不过是揭示这个楼是怎样歪的、为什么会歪。文学本来不就是这样复杂、迷离、多元的吗?因此,对文学也不存在唯一的解释,文学研究不是为了得出唯一正确的答案,否则那将是多么无趣,也远离了文学的本质。
大学教育和文学研究,都要打开、打开、再打开
史书是这样写的,读史的人也是这样读的,关注点往往放在宫廷政治和在那样一种政治结构下的钩心斗角。我很希望年轻人不要再用这种传统的方法、趣味去看历史
读书周刊:您一直强调文学、文学史研究要回应现实、回应当下,体现现代人的态度,有自己时代的问题意识。从《〈三国志〉讲义》到《〈洛神赋〉九章》,您对这些古代经典文本的研究有着怎样的现实关怀?
戴燕:我以前讲《三国志》,比较多采用文化史的方法,而不是讲一个王朝史。20世纪之初,梁启超曾把中国的传统历史书写称作“帝王家谱”“相斫书”,批评它们“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史书是这样写的,读史的人也是这样读的,关注点往往放在宫廷政治和在那样一种政治结构下的钩心斗角。我知道自己的力量薄弱,可是很希望年轻人不要再用这种传统的方法、趣味去看历史,而要用我们自己时代的眼光。所以,我没有按照最流行的《三国演义》方式讲三国,而是更多涉及民族、女性、医学等话题,我想学生也许能在这些话题中找到与自己的个人生活、个人经验以及所学专业相关的内容,能够启发他们真正地去与三国史对话。
我讲《洛神赋》也是这样,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解读,帮助读者调动自己的经验,来读《洛神赋》,最后也形成自己的看法。当曹植用他无与伦比的才华和极其华美的语言铺陈描写与洛神的邂逅,以表达克制守礼这一主题时,他纵情奔放的笔法,就已经突破了守礼的主题,使后来的读者忽略了他原有的宗旨,而产生了极其丰富的联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已有的丰富解读之上,加入自己新的解释。这就是文学和文学的传承,一个文学传统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之所以决定尝试用一种新的方法解读《洛神赋》,当然也是因为看到在一千多年后,《洛神赋》依然有这么强的生命力,是活的文学,因而得到一点“后见之明”。也许同我不习惯偷懒也有关系。
读书周刊:您的“不习惯偷懒”,接近于您对《陟彼景山》中11位被访者的评价。您曾说,这些一流的学者都是“整天干活的人”。
戴燕:只要看看他们的学术成果,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比如何兆武先生,他翻译了那么多书,写了那么多书,总有几十种吧,却谦虚地自称“边缘人”。
这些学者有这么高的学术成就,这么多的学术成果,靠的是什么?就是干活,就是出力气。不过我不能跟他们比,他们都是真正有贡献的人,我仅仅是学到了出力气这一点。
读书周刊:不仅“干活、出力气”,您还曾谈到,这些学者好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具有跨学科的能力。比如李学勤先生和裘锡圭先生,都是顶尖的上古史专家,可有意思的是,李先生不但英文很好,还曾学过俄语,曾有志将中国古代和外国古代做一个比较性的研究。裘先生则会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思想。您自己也一贯倡导和实践文史不分家,您如何看待今天大学里越分越细的专业设置、学术界越分越细的专业研究?
戴燕:跨学科的说法,本身就很有意思,学科本来就是人为划分的,如果我们没有在学科之间筑墙,何来跨之说?中国现代学科设置,最初是受欧美影响,后来又受苏联影响,这一点我在《文学史的权力》里讨论过。分科对于一些现代学科的成长有好处,但是在进行传统文化研究时,也造成不少麻烦。我刚刚进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困惑,因为专业分得太细,后果就是把那些文学经典悬置起来了,文学史也被切割得七零八落。
还好我大学读的是古典文献,在我们这个专业,文史哲不分家,这对我后来的思考和研究影响很大。
读书周刊:过于细分的专业设置,也许会影响一个人世界观的建构。
戴燕:人们有时候会有个误解,以为专家就像工匠一样,只专注于某一个领域,但是这么多年来,我有幸接触到一些优秀学者,深刻感到一个人学问的高下,或者说一代学人的整体风格与成就,同这个学者或他这一代学人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有关系。大家读《陟彼景山》的话,是可以发现这一点的。
我的世界观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我这一代人,大多是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阶段,能看的书越来越多,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人与人相识,国与国交流,障碍逐步减少,机会逐步增加,我个人也在这几十年里慢慢开阔眼界,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丰富和多元。这样的经历自然影响到我的研究,我是做古代研究的,每天都要“摸”古代文献、和古人打交道,但我从来不会想象自己是在与“青灯古卷”相伴,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个现代人,因此总是希望能沟通现代和古代,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融入现代观念、现代方法,讲现代人听得懂的语言。
曾经有一个说法,强调文学是陌生化的,如果同意这一点,那么文学研究也应该是能带来陌生化的,就是要不断给出新东西。文学本身就是不保守、不僵化,没有条条框框,永远在变化的,我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当然也希望能在自己的研究中尊重和传达文学的这一特点。特别是作为一名老师,我想我的责任就是帮助学生打开自己,一再地打开自己,就像老子说的“旷兮其若谷”。打开自己才能接纳万物。



